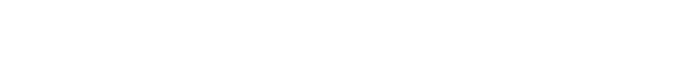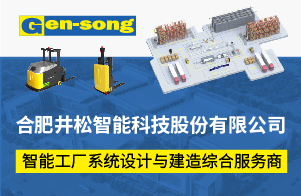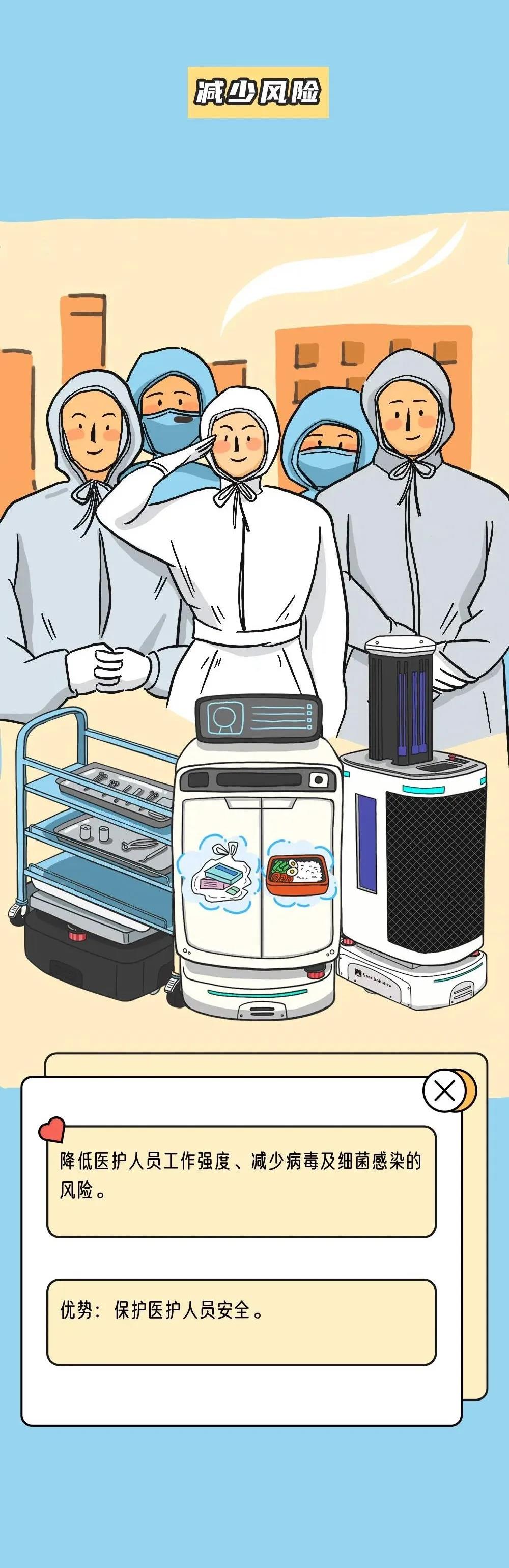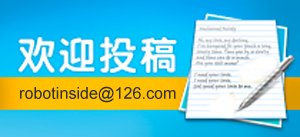納米磁性粒子,聽起來有些復雜,如果換個通俗的說法,那么谷歌這個新項目其實還有另一個更耳熟的稱呼–納米機器人。
納米機器人的概念最早并非源自谷歌。目前比較普遍的說法是,它由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理查德·費曼在1959年一次題為《底層有很大的空間》的演講中提出。
理查德·費曼認為,人類未來有可能建造一種分子大小的微型機器人,可以把分子甚至單個原子作為建筑構件,在非常細小的空間里構建物質,這意味著人類可以在底層空間制造任何東西。
理查德·費曼提出的微型機器人概念,確切地說應該屬于納米機器人,即本身體積可能超過了納米級別,但所能操控的物體屬于納米尺度。如今谷歌正在研發的納米機器人,則是指自身體積在納米級別內的機器人。
不過,不管是納米操作機器人,還是納米機器人,本質上都是根據分子水平的生物學原理為設計原型,設計制造的可對納米空間進行操作的”功能分子器件”,屬于分子仿生學的研究范疇。
雖然個頭小到分子級別,肉眼根本看不見,但納米機器人實際作用卻十分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醫療衛生應用–檢測消滅疾病。
這也是在眾多科幻電影中展示最多的一項功能:當你感冒發燒,醫生不再是給你打針吃藥,而是在血液里植入納米機器人,這種機器人在體內探測感冒病毒的源頭,并達到病毒所在處,直接釋放藥物殺滅病毒。
不只是感冒發燒,在同樣機理下,精確找到并殺死癌細胞、疏通血栓、清除動脈內的脂肪沉積、清潔傷口、粉碎結石等,都會是納米機器人這個”未來體內醫生”的拿手好戲,這些功能中,每一項都有可能變革整個醫療行業。
更為不可思議的應用,是將納米機器人當作媒介,連接人腦神經系統和外界網絡系統,為開發人腦智力和潛力帶來無法想象的革命,徹底改變生活和工作方式,甚至是人類本身。
納米機器人現實難題
雖然想象無比美好,美國、日本以及中國一些研究機構也都成功研發出了應用于各種疾病檢測治療的納米機器人,但迄今為止,納米機器人技術依然停留在研發試驗階段,還沒有哪個項目的成果真正進入臨床。
谷歌的納米磁性粒子同樣如此,安德魯·康拉德坦言,雖然谷歌同時還在開發一種磁性可穿戴式設備,用來計算這些納米粒子的分布,但對于如何引導粒子機器人到指定的目的地、或者綁定特定的目標細胞,目前也還沒有成熟的解決辦法。
科研人員還沒有給納米機器人找到成熟精準的”導航系統”。比起現實世界的城市或公路網絡,人體內的靜脈和動脈網絡要復雜得多,而且納米機器人如果不停留在人體內,就必須為它找到合適的出口。
另外一個問題同樣難住了科學家們,即納米機器人的動力系統。納米機器人的體積已經是分子級別,在這種情形下,制造一種更小的電池放進納米機器人體內變得極其困難。
即使成功制造出這種納米級電池,在當前電池技術水平下,電能大小與體積直接相關,過小的電池體積也注定了這塊電池無法滿足納米機器人完成任務所需要的能量。
除了這些技術障礙,技術監管和社會意識的風險同樣不容忽視。谷歌的納米粒子機器人初步設計以藥片的形式提供,吞服到人體內,就意味著將面臨比體外各種檢測儀器更嚴格的監管力度。
而在人體內24小時不間斷檢測數據的做法,也會讓谷歌以及納米機器人面臨不少質疑。在此之前,谷歌等企業收集用戶隱私的行為已經廣受抱怨,納米機器人深入人體,更容易讓人產生更為可怕的聯想。
納米機器人突破方向
以上問題導致納米機器人的現狀一直不溫不火,但這并非意味著納米機器人沒有未來。
技術層面,目前看來,導航系統的難題正在得到解決。研究人員已經從內部和外部找到了不少可以進一步尋求突破的方案。
內部的導航方案即納米機器人自帶傳感器。得益于納米技術的發展,傳感器如今的技術水平也有了質的飛躍。為納米機器人配備化學或者光譜納米傳感器,就能夠探測并根據特定的化學或光感追蹤技術,找到正確的位置。
外部的方案更多,可以向納米機器人發射超聲波信號、無線電波、X射線,引導納米機器人的走向。當然也可以采用谷歌的解決方案,使用配套的可穿戴設備,利用磁場來指引道路。
動力系統的解決辦法則麻煩一些,有研究人員想到了利用血液中的電解液作為能力,通過納米機器人自身攜帶的化合物與血液反應產生能量。還有研究人員提出可以使用核能,解決了體積和能量的矛盾,不過由于公眾對核能固有偏見,真正應用中很難被采用。
現實社會的監管和道德問題看似很復雜,但實際上只要有合適的契機,同樣有可能快速取得突破。
“想想看,如果人們可以通過納米機器人系統自行完成醫療診斷測試過程,誰會不希望更快地加入其中。這背后,又能產生多少新型的巨大的商業機會。”安德魯·康拉德說。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有一個綜合所有最優技術的、成熟的、臨床可行的納米機器人解決方案。